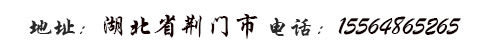世界读书日特刊兰善清书里的乡土
|
书里的乡土 文/兰善清 时常从阅读中感受乡土气息,获取乡情濡沐,博得乡愁慰藉。天之大地之广,也许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但往往又乡情无处不在,所见无所不亲,毕竟都生活在岁月的屋檐下,衣食住行大同小异,社会化的小圈子又包容在大圈子里,书和其他文明都是通向每个人的,贴近每个灵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共情就理所当然,阅读走向心灵的故乡。 英国作家约翰?伯格《猪的土地》有段写到工业文明和城市化之下的乡村情景:“村里很多男人去了巴黎挣工资,做伙夫、搬运工或扫烟囱。离开前,男人备好足以过完复活节的干草、木柴和土豆。留下来的是女人,老的少的。冬天我没父亲几乎没人留意,跟我同龄的一半孩子暂时都没父亲。”看到这里,我立马就联想到我的故乡这几十年的情形,壮劳力涌向城市,留守故土的是张大妈李大爷以及他们的孙子孙女,我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迟了西方,但最终我们快步跟上了,重温他们的那时候也就是具体感受我们的当下。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梳理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中有关乡村与城市的种种描述,在驳斥那些缅怀旧日农村的错误观念时,所提到的工业化形势下的大量的乡村空壳化现象,也非常叠合我所经历的我们乡村的这些年。看来,历史进程中的必经之路都有一定的共性。 读德富芦花的《春天的七日》,其中一篇《远离都市》一段记述引起了我的共鸣。他写到:“明治初年,离开距萨摩很近的故乡搬到熊本,后来又从临时借居的亲戚家搬到父亲买来的破茅草屋。出生四十年来,我也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和茅草屋,我感觉自己仿佛成了帝王,舒舒服服的伸展双脚安然入梦了。”住茅草屋就知足的日子,我家就实实在在经历过。常听我的哥说,爷爷那时候,没有立足之地,寄人篱下,后来亲戚给了一爿地,盖了两间茅草屋,一家人从居无定所中安顿下来,欣喜若狂,夜不能眠。阅读德富芦花才知道,茅草原来不仅长在我的故土,也长在日本的乡下。当然,也长在唐朝的成都郊外,不然,杜甫怎么会有那被八月秋风卷起三重茅的草堂呢!也长在十八世纪英国诗人汤姆森的家乡,否则,咋会有这样的诗句:“我清楚记得这些羽毛/这些野草/和墙上的针茅/被雾和安静的雨珠镀成了银色。”其中的“针茅”不就是我们这里的鸿茅? 赛珍珠曾扎根中国乡土,她的《大地》写了逼真的江南农村生活,其中一段关于夏收的情节中出现了“连枷”的农具描写,这一下子勾起了我不远的记忆。我母亲、我嫂子、我的乡亲们在麦场脱粒时,都使用这工具,祖祖辈辈都是靠这工具将麦穗脱出颗粒的。要说江南人使用这工具应该不足为奇,我们鄂西北距江南不远,地畔相连,风俗相近。而在德富芦花笔下出现就有些新奇,他在《梅雨转晴》一文写到:“一直盼着放晴的农户也雀跃不已,纷纷开始打麦子,耳边充斥着劈劈拍拍的连枷的回响,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这更酷似了我家乡那些年的麦收情景,“劈劈拍拍”的声音让我更具体的看到了那“连枷”即我家乡打麦场上的那个挥起又重重落下的带着浓重夏收气息的工具。 简媜也善于写乡村生活,她在《漫卷心情》一文里写到:“从前在家里煮饭,灶前一面看火一面看书。”看到这句我的童年一幕就出现了,小时候,母亲忙活做饭,我就帮忙烧火,那些松针杂草类的柴,添进灶内,火苗一起,轰的一下子就没了,还没看完一行字,就得立马再去添柴。一心二用,许多次,喷出的火苗把头发和眉毛都燎焦了。 迟子建在《灯祭》里写到当年她父亲用玻璃罐头瓶给她做灯罩的细节,顿时让我找回了我的从前。灯在外面提着是需要灯罩的,用布或纸糊的罩子不经用。当生活里出现了玻璃罐头瓶时,这就成了最佳灯罩。玻璃瓶底怕开水烫,一烫底就掉了,圆筒就成了最好的灯罩。这法子我在住校读书时就用了,迄今那烟熏火燎的黑不溜秋的灯罩还在我的眼前不时的晃悠。 汪曾祺在《冬天》一文写到:“天冷了,床上拆了帐子,铺了稻草。不过还是冷的,南方的冬天比北方难受,屋里不生火,晚上脱了棉衣,钻进冰凉的被窝里,早起,穿上冰凉的棉袄棉裤,真冷。”冬天床上铺稻草,这正是我们这里从前的做法。也用草绳制成稿荐(这个种物品我以为就是我们当地制作,后来在周同宾《皇天后土》里看到,才知道它不局限于我的家乡)铺上,这“稿荐”也就是床垫子。汪先生说的晚睡早起的冷,我也感受至切。小时候冬天总是圪蹴在火炉边不愿意先去暖被窝,早上母亲催了又催总怕挨着那冰凉的棉袄,母亲有时候会把棉袄棉裤先拿到灶火上烤烤,催我:“快起,快起,暖和和的,一会儿就凉了。”这时才一骨碌爬起,三下两下,左一捅,右一捅,噔的跳下床,那一刻的冷如此就过去了。 风俗习惯上,各地也会有许多不约而同的东西。汪曾祺《昆明的雨》说昆明人常于门头挂仙人掌避邪。我记事时我们那间草房顶上就栽了大片仙人掌,问做啥用,母亲说避邪,父亲则说是贴毒疮用。无论哪种作用,就不清楚这个南方植物怎么跑到我们这接近北方的土地上来的,现如今它已生活下来了,有了我故乡的风味。 沈俊峰的《自信的文化土壤上》写到安徽那里的乡俗,闹洞房“三天不论大小”,重视文化教育的口头禅是“穷不丢猪,富不丢书”。这也是我们这里的习惯说法,且自古流行。新娘子入门三天,为了图个喜气和热闹,长辈晚辈都会放肆的开玩笑,厮闹。在持家上,养猪是致富的首要途径,教育孩子读书是升起生活希望的唯一出路。沈俊峰还特意用到一个形容笨、傻、憨的地方土语“苕”,这个词在他的《水》一文中看到时很是好感,觉得是我们身边人在说话,我们这里常说:“你别苕啊,放聪明点!”一个土得掉渣的词居然在江淮也用,这就有了把千里之外的皖北引为同乡的冲动。 我也常常把文艺作品视为书读,比方一个相声小品、一部电视剧、一部喜剧或电影,像翻书一样看得仔细。当年看马季与他两个弟子合说的一个相声《一仆二主》,其中带出了个有音无字的方言词“bia”,听了倏然一震:这个词不是我们这里的么,怎么出现在诞生普通话的北方?我还以为只有我们鄂西北土话专有呢。我们把“粘”、“贴”、“糊”叫“bia”。这词很有动作感,打田埂时将泥巴贴上就说“bia”上,糊墙,贴年画就说“bia”墙,“bia”年画。这个方言词在西北也使用,相声演员苗阜和王声在一个相声段子里就用了,这让我在北方方言区里听到了乡音。赵丽蓉和李文启、巩汉林演的一个有名的小品《妈妈的今天》,赵丽蓉一句有名台词:“探戈就是趟呀么趟着走”,她特意把“就是”说成“做是”,其他方言区的人听来也许不太留意,而我们鄂西北人就听得特别真,因为我们经常把“就”说成“做”,“我做是不去,你把我咋啦?”在我们的方音里有些词语还保留着古声母音,“就”说成“做”音。古声母“z.c.s”后来分化出今音“j.q.x”,“就”的古音声母属于“z”,读“做”,分化成今音“j”读成了“就”,今天受普通话影响我们也把“做”说成“就”,但“做”的古音在方言里依然在,所以听到赵丽蓉这个咬字时,我特别上心。一次听周迅与喜剧演员阿星演小品时将“吓(xia)”说成“嚇(he)”,“啊呦,好吓(he)人的。”很是亲切,这也是我们这里的方音,我们时常把“吓人”说成“嚇人”。这也是古音分化的后遗症。历史上的“g.k.h”分离出“j.q.x”时,我们方言区保存了部分古音,所以,现今“吓”的古声母“h”与今声母“x”读音同在。也许历史上我们两地在一个方言区,一听就觉得周迅说的是我们这里的话。 也许乡亲在他乡,也许乡土在远方,读书找去吧! 书和一切文学艺术反映了最广大的人们生活,所以,我们可以翻页遇到老乡,携手走进村头老屋。 作者简介 兰善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随笔集《笔照心海》《我写故我在》《万古一地》,主持编写纪实文学《创业之路》《浴水重生》《郧阳雄风起长岭》等。在《中国作家》《长江文艺》《芳草》《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散文百家》等报刊发表作品。其中《有家才成人》《命运》《一晃三十年》《笔的进化》《我的人生我的酒》等作品在全国各类散文征文比赛中获奖。 三槐堂上海书简 高级顾问:(以受邀时间为序) 梅洁野莽王家新王祥夫 聂鑫森王剑冰阿成孔见 法律顾问:邓学平 特邀指导: 兰善清王国荣马富国 主编:王成伟 责任编辑:雾月 特邀编辑: 袁冰洁贾斯炜肖江 美术编辑:王鹏 请扫下面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iangfencaoa.com/lfcxgls/8744.html
- 上一篇文章: 进家门忌讳见到什么很多人不知道
- 下一篇文章: 基地地栽多肉植物苗批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