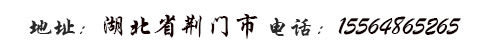张旭看草书仙人,酒后书真情,无狂不成书
|
白癜风检查 https://m-mip.39.net/nk/mipso_4461452.html 他以草书著名,时称张颠。 他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 他是唐代书法家、与怀素齐名。 他的诗别具一格,以七绝见长。 他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 他好饮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 他与李白诗歌,裴旻剑舞,称为“三绝”。 他与李白、贺知章等人共列饮中八仙之一。 他又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号称“吴中四士”。 他是草圣张旭。 前言: 张旭三杯草圣传, 脱帽露顶王公前, 挥毫落纸如云烟。 一 身边有位认识了很多年的书法前辈,平时喜欢喝点小酒。每次相聚一起吃饭喝酒时,先生都会聊点喝酒与书法的关系。酒劲上来以后,人的书写容易出感情。然后,手随心动,写出来的书法作品当然是真情实感的体现。 比如《兰亭序》的创作,相传就是王羲之在兰亭雅集上喝了足够多的酒之后创作而来的。也有人说,待到王羲之酒醒之后,在清醒状态下在去书写,则完全不出酒醉中的效果了。 三杯老酒下肚后,真言吐露的同时,书法感情也被酒精给催发出来。这应该就是先生提到的酒精与书法的关系吧。当然,书法感情的流露未必总是依靠酒精来达到。比如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可问题在于,如颜真卿写《祭侄文稿》时所遭遇的那般国破家亡的悲痛,怕也不是普通书家、普通人所能有机会体会的。尤其是和平盛世之中的书家似乎只能借助酒来催化自己的感情了。 唐代张旭就是这样一个依靠酒精可以将其书法魅力发挥到极致的书法家。 二 然而,就是这个性好酒的男子,却有著惊人的履历: 与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合称“三绝”。 与李白、贺知章等共列饮中八仙。 在开元时期,就以诗文之名名世, 与贺知章、包融、张若虚并称“吴中四才子”。 诗亦别具一格,以七绝见长。对艺术极其痴狂,被后世尊称为”草圣”。 三 “饮中八仙”里,张旭其实是最接近于仙的。 不仅因为他的潇洒不羁,还因为他的来去无踪。至今也没人搞清张旭的生卒年月,我们只确切地知道,他活在盛唐。 张旭,按照现代历史学家闻一多先生的考据材料,其出生于公元年,卒于年,享年应有89岁,这只能是一个约数,其活动年代应是唐开元、天宝年间。 他的官做得并不大,为太子左率府长吏,这个官名的职责,应属太子门下的僚属跟班之类吧,其官名品位只是一个相当七品,与实职的知县一类七品仍有差别。 四 张旭以草书名世,然而写狂草的他,却练得一手精绝的楷书。 应该说,张旭之所以能成为书法大家,那是有著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家庭环境。我们知道,科学家的子女成为科学家的概率肯定要比一般家庭高得多,比如居里夫人家。依此类推,书法世家出生的孩子自然要比普通人家的孩子更能成为书法家,你要不信,看看田润章、田英章两兄弟的家世背景就知道了。 张旭就是这样,其母陆氏乃是初唐书法家陆柬之的侄女,也就是虞世南的外甥女。虞世南大家都应该听说过,他不仅是唐太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而且也是位书法大家,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为“唐初四大家”。 出生在这么一个书法世家中,加上其母陆氏以书传家,因此他从小就学太姥爷,得其笔法,颇类晋人。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之所以能成为“草圣”,是源于他的后天努力与性情所致。 五 草圣张旭的一生,犹如神龙不见首尾。却又是极致的单纯简易,化约为“酒”与“书”两个字。 李白斗酒诗百篇,怀素醉酒轻世界,张旭也比他们先醉了几十年,而且醉出一个“草圣”的大名头。 就因这草圣之颠,吸引了盛唐无数诗家的目光。一种诗与书法结合的现象出现了,一种诗人与书法家的融通文化现象出现了,一个酒与狂草的狂醉文化现象出现了。这就是盛唐文化现象,奔放不羁又情致激腾,风流敏丽又雄浑沉着。 欧阳修主撰《新唐书》,其中《张旭传》开篇即如是:“旭,苏州吴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这篇传文仅字,真是惜墨如金,但开篇这40字除“苏州吴人”外,全着墨于张旭酒事了。 六 张旭性格豪放,嗜好饮酒,常在大醉后手舞足蹈,然后回到桌前,提笔落墨,一挥而就。 有人说他粗鲁,给他取了个张癫的雅号。其实他很细心,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所触到的事物,都能启发写字。偶有所获,即熔冶于自己的书法中。 当时人们只要得到他的片纸支字,都视若珍品,世袭真藏。那时候,张旭有个邻居,家境贫困,听说张旭性情慷慨,就写信给张旭,希望得到他的资助。 张旭非常同情邻人,便在信中说道:您只要说这信是张旭写的,要价可上百金。邻人将信照着他的话上街售卖,果然不到半日就被争购一空。邻人高兴地回到家,并向张旭致万分的感谢。当时人们把张旭的草书与李白的诗词,斐旻的剑舞合称三绝。 张旭每次饮酒醉时就草书,挥笔大叫。将头浸入墨汁中用头书写,酒醒后看见自己用头写的字,认为它神异而不可重新得到。后人评论书法名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臣、薛稷四人,或许有不同的意见,至于论到张旭,都没有异议。 七 张旭能夺得“草圣”之头衔,没有一流的技艺,没有慑服众人的精神,那是不可想象的。 在书法的道路上,张旭走的是一条完完全全的传统学书之路,他的楷书也十分有名,相传为其所书的传世楷书作品有《郎官石柱记》,后世誉为唐楷第一。 有了一流的楷书作为功底,才子张旭才敢在姿性任情的草书领域驰骋走笔。草书之妙,前人已有榜样,从汉代张芝一路下来,到东晋王羲之、王献之,只要花功夫、肯琢磨,自会有好收获。这种收获有时带着非常大的偶然性,辛苦一辈子,可能一无所获,有时悟性一到,却会一步踏进神逸之境,这就是艺术,艺术就是捉摸不定的学问气象。 盛唐的才子追求的是盛唐的气象,诗歌一流,草书也一流,盛唐占尽了文学艺术的顶尖风流。李白诗狂,怀素书法也狂,但张旭草书之狂比他们都早狂了几十年。这“草圣”之名,是历史性地落到了张旭的头上。 八 张旭的草书为什么那么狂,而且能狂到如此的艺术高峰? 盛唐书法在继承魏晋与南北朝诸书法流派的优秀传统基础上,与诗歌艺术一样,形成了一种充满生机和活力,蓬勃饱满的“盛唐书风”,这一时期,书作流美遍地,名家相集成群。在书法上,要想在盛唐期间出人头地,并非易事。 张旭的草书看起来很颠狂,但章法却是相当规范的,他是在张芝、王羲之行草的基础上升华的一种狂草。细观察其书体绝无不规则的涂抹,很多细微的笔画、字间过渡,都交代得清清楚楚,绝无矫揉造作之感。 张旭的草书是在激越情感牵动下促使节奏加快,似金蛇狂舞,又如虎踞龙盘,表现一泻千里之势。由于在线条的动荡和质感上加入了盛唐的艺术气息,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狂放的草书风格。 盛唐的艺术,树起了无数的颠峰,单是草书,也不知吸引着多少人去潜心创造,但没有多少个人可以轰轰烈烈地留传后世,为什么?这正是草书的奥妙之处,它飞动中的稳健和凝重,飞动中的法度和不可重复性,要使它形成合理和合法度的浪漫主义艺术十分艰难。 无数自诩弄通了草书的大书法家们,实际上都在犯着不能形成“自然之妙”艺术高度的错误。因为他们的执着和先入为主的创造心态正是草书创作的大忌。一两笔的得意之作是不能构成“神逸”的草书的。而张旭的神逸草书正是他不自觉的“无意于佳乃佳”的作品,而且能传世的也就是有限的那么几幅。这正说明了古人所称的神逸之品形成的艰难。 九 翻阅张旭的草书,最成功的应该是他的“古诗四帖”。 这幅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线条中活活泼泼的生气,通篇体现着一种十分自然的形成过程。如果我们不服气,可以拿笔临一下,不论你是多么高明的仿真高手,临出来你才会发现漏洞。草书的不可重复性,使其成了书法最高最难的艺术颠峰。一切认为草书可以随心所欲的所谓大书法家们,只不过是自负心理在作怪而已。 张旭的草书当然不是中国草书的颠峰了,后来的狂僧怀素,就是在学习张旭草书的基础上有了改进,将张旭草书中平直的线条作了弧形的处理,使其缭绕之气更具流畅的韵味。但张旭的草书与怀素的草书是两名大草书家的作品,其风格和构成都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只要书法有了一定深度的书家都可体会出来。 张旭的嗜酒和忘我之境实际上是他自信与自恃的性格决定的,当时外界的一切压力和有利条件也是促成张旭性格的因素,所以独特的性格和独特的环境决定了张旭独特的草书艺术。 十 传说中,张旭每每喝酒酩酊大醉之时,则是其草书创作的最佳时机。相传张旭甚至在酒后豪迈之时,以头发蘸满墨汁书写。不过这种说法很有可能是后人杜撰而来的。 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驳斥这个观点,还挺有道理,文章说,唐代造纸工艺恐怕还不能造出那么大尺幅的纸张供张旭用头发来泼墨书写。不过,不论这个传说是否真实,我们确都从这个传说中看到了张旭那种酒后癫狂的举动。所谓“颠张狂素”,张旭的癫狂就是在酒精作用之下的表现。当然,这种癫狂之举,也已经成为张旭留在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符号记忆了。 精与癫狂是一对孪生兄弟,文人可以借助酒精来癫狂,也可以因癫狂而肆无忌惮的饮酒。虽然后来,癫狂似乎慢慢离开了酒精而独门独户,自己成家。但是,起码在唐代时候,他们两者还不能分开。 唐代张旭和怀素,之所以被成为“颠张狂素”,怕是与酒精都有不解之缘。正如我提到的,张旭斗酒之后就会用头发泼洒翰墨,这种潇洒就是一种癫狂。 十一 其实最能代表中国书法艺术的是草书,因为它使中国文字由实用性的书写工具上升为情感寄托的载情艺术,而书法的觉醒和追求则是以草书确定为前题的,使人们在实用之外有了更多的遣兴。 张旭是古今以来草书艺术家的典型代表,他不光有深厚的书法艺术素养,而且在表现上把自己激荡的感情和书法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张旭借狂草来抒发个人情感,其实体现了盛唐时期艺术家们的思想情结和普遍的精神风貌。这是主观意愿和客观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使反映情感的书体得以最完美的发展。 张旭书法惊涛骇浪般的狂放气势,节奏韵律的和谐顿挫,字间结构的随形结体,线条的轻重枯润等变化都达到了草书的最高水准,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出现影响了后来历代几乎所有的大书法家。当今书法这一艺术门类在广大群众中研习相当普及,《古诗四帖》不乏为学书的极好范本。 十二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禁不住又兴致勃勃地翻看张旭的“古诗四帖”,醉心于它的自然之妙。 至于说他悟得的什么“公主与担夫争道”、“公孙大娘舞剑器”之类的说法,我却觉得有点后人的牵强附会,或者是张旭酒醒后要将自己的草书蒙上一层神秘色彩的故弄玄虚吧。自然之妙是不能先入为主的,如果说,“古诗四帖”的挥运之妙有书家能够悟出,那这种悟出也是书家自己挥洒的形象,并非张旭。 真正的张旭在醉态中会知道自己怎样挥运吗?想当草书大家的书法家们,喝醉了就有体会了。 文/鸶图片来自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 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 ——《桃花溪》张旭 山光物态弄春辉,莫为轻阴便拟归。 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 ——《山行留客》张旭 旅人倚征棹,薄暮起劳歌。 笑揽清溪月,清辉不厌多。 ——《清溪泛舟》张旭 春草青青万里馀,边城落日见离居。 情知海上三年别,不寄云间一纸书。 ——《春草》张旭 张旭《古诗四帖》28.8cmx.3cm 书画赏析 古诗四帖 张旭 唐代 狂草 纸本五色笺,墨迹 纵28.8厘米,横.3厘米 40行,字 辽宁省博物馆 《宣和书谱》、《续书画题跋记》、《式古堂书画汇考》等著录。 《古诗四帖》墨迹本,五色笺,狂草书,共40行、字。传唐代张旭书,尚有争议,但它是张旭笔法系统中一件重要的作品。大部分线条不强调提按,而重视粗细均匀的线条中使转与速度的变化。通篇笔画丰满,绝无纤弱浮滑之笔。拖尾有明丰坊、董其昌题跋。通篇笔画丰满,绝无纤弱浮滑之笔。行文跌宕起伏,动静交错,满纸如云烟缭绕,实乃草书颠峰之篇。 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到其他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iangfencaoa.com/lfcxgpw/8887.html
- 上一篇文章: 爽吃37元的螺满地,用37折的敷尔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