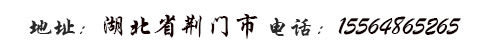下放在巢县钓鱼台印象最深的那些人上
|
原题:“半知青部落”轶事 前言 年的春天,来得似乎有些早。这不,刚过了惊蜇,三月八日的巢湖,已是“和风丽日景正好,又到踏青出游时”了。 大弟驾车,从合肥出发,四人同行,驱车百余公里,探访我昔日下乡插队的林场,当时叫巢县银屏区钓魚台林场,现在叫望湖山林场。 下了高速路后,驶过巢湖市区。……车窗外,平缓的裕溪河,绵延至远方。大大小小的运沙船,划破了宁静的水面。望着远处越来越近的望湖山,思绪飘渺,有些恍惚…… 钓鱼台,应该不是姜尚钓鱼之地,他垂钓于渭水,来不到这儿的;有说是仙人李浮丘垂钓之地,故名“浮丘钓台”;也有说高人范增出居巢辅佐项羽之前,曾在此垂钓。总之,此处垂钓者皆非等闲之辈,故此地也绝非寻常之地。 那年的中秋夜,皓空当空,大河如练,我与好友涛枯坐于钓台,没有酒菜,甚至连一块月饼都没有。身下的整块石板上,留有当年“仙人”“高人”垂钓时的遗迹:放置钓竿的石槽,脚下有他们坐下时蹬出的“脚窝”。我们没有钓鱼,与鱼无关,而是就着中秋明月与静静的河水,伴着夜风,畅谈理想与人生,在“钓”未来。这也许就注定我们成不了仙人,也成不了高人,只能是寻常人——尽管涛后来在京城干到了副部长级…… 遥想当年,凝望眼前,山河依旧,壮志豪情似水流,流走了,人老了,老眼昏花,其实,老了容颜,更老了心志…… 那时的我们多年轻啊…… 年,牵扯着千家万户神经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几近尾声。年元月,我们拍完了从铜陵二中毕业的合影照,赖在家里呆了两三个月,实在赖不下去了。正巧,当时,冶金部华东冶金地质勘探公司新组建了队,驻地巢县。队与钓鱼公社联系,以“队社挂钩”的形式,为本队应下乡的子女在林场搞了个知青点。当时,父亲已先期到工作,家却还在铜陵队没有搬。四月份,我和境况与我相同的10多个同学一道,离开铜陵的家,渡过长江,到了江北的巢县钓鱼台林场。当时,队上对我们说,我们下乡时间不长,短则三个月,长则半年,很快就会内招我们进地质队。结果,我们连头带尾,在林场呆了八个月。那八个月,尽管蜻蜓点水般,于我却大有裨益,至今难忘。 我下乡的林场,人不多。20多个知青,其中男知青十四、五个,涛与另外三、四位是巢县当地的;女知青七八名。为了加强对我们的“再教育”和管理,公社又从生产队抽调了十来名贫下中农,加上不脱产的党支部书记、场长、会计,还有专职的司务长兼饮事员,在远离村镇的山脚下,组成了一个近40人的小“部落”。我将其称之为“半知青部落”。 近八个月的“半知青部落”生活,留下了许多值得我一生咀嚼回味的记忆。 现在,我就来唠唠我记忆中最深的那些人与事吧…… 一、印象最深的那些人 1、场长 场长姓冯,名文美,冯文美。我一直很好奇,这老头他咋叫了个那么秀气的名字? 老场长给人的印象,就是标准的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一顶灰旧的帽子,一张沟壑丛生的方脸,一双平常昏浊无神重要时刻却很犀利的眼,灰旧的四个口袋的上衣,灰旧的裤子和一双旧的解放鞋,永远肩着一把铁锹或锄头,嘴上的香烟袅袅着…… 那时,我觉得他很老了,至少得有50岁了。他的家住得很远,得翻几座山。所以,他很少回家,办公室兼了卧室,紧挨着我们男生宿舍。他的老伴、儿子和媳妇来看过他,好像还带来了小孙子。 老头人特好,我们都打心眼里喜欢他,敬重他。老头人好,并不是说他没脾气滥好人,他发起火骂起人来厉害着呢!我和几个年纪小的调皮的搅在一起,惹了不少事。惹事后,总是被他骂得要死。被他骂的那些事,我在后面还要说。但老头心眼好,骂归骂,也从心里疼我们,是那种父母疼自己孩子的疼,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 我那时很瘦,个子也没长起来,但饭量奇大,特能吃。每人每月30斤的粮食定量,买成饭票,在食堂打饭,根本不够吃。这一情况,在我们到场后的第二月,老场长就晓得了。有天晚饭时,大家端着碗,或蹲或站,都在吃饭。老场长围着我转了几圈,自言自语道,就你,瘦得跟小鸡仔似的,有那么大的饭量?旁边的饮事员老李,我们都叫他李师付,平时是个闷葫芦,不爱说话,也很难说话的一个人,那天竟然接了老场长的话茬说,他就是能吃,前天晚饭吃了一斤四两。冯场长一听,问道,多少?一斤四两?嗯,先打了个半斤的,没吃饱,又打了个半斤,还没吃饱,第三次来打饭,饭没了,只剩锅巴了,打了四两锅巴,加了点盐,撅了一筷头猪油,开水泡了,又吃完了。冯场长听了,看着我,那你30斤的定量肯定是不够吃喽?我很不好意思,挠着头说,嗯,不够吃,从家里带了点粮票,也差不多用完了。冯场长没言语,点了点头,随即问老李,还有谁的饭量大?老李说,还有就是小滕了,他俩饭量都大。 老场长点了点头,立定了脚步,声音不大,很清晰有力地说道,那就这样吧,从这个月开始,小滕和小耿的定量,每人每月由场里补助15斤,每人每月45斤,咱们不能让这俩小子饿着! 别小看那15斤定量,凡是关系到肚皮的问题,那就是天大的问题。 我记住了老场长的这份恩典。10月底,我们回去做招工体验,我向家里要了烟票,给老场长买了两条大江牌香烟,那是我能买到的最好的烟了。不为别的,只为他老人家待人的那份真诚。11月份,我们招工回城,离开了林场。 2、书记 书记姓王,叫什么忘了。王是场党支部书记,年纪不大,估计不到30岁,但显得很老成。 王书记是个退伍兵,在部队入了党,却没能提成干,退伍回到村里,干了几年,当上了大队书记。公社建这个林场,抽人,将他调过来当书记。 他虽然是书记,我们大多不喜欢他,也说不上讨厌,更无恶感,对他都是敬而远之。反正我们很快就会内招回去,只要不犯大错,犯不着迎合巴结他。当然,那几位巢湖地区和巢县的知青,还是很迎合他的。 我们不喜欢他的原因,首先是他的长相不讨喜。人是一面相,他的相叫人难以喜欢,太像《地道战》里的那个汤司令了。“高,实在是高!”影片中念这句台词的伪军司令,嘴虽难看,还没有我们王书记的那一嘴大黄牙。那时的我们,以貌取人的错误很严重!再说了,他年纪轻轻的脑袋也秃了,大热的天,戴着黄军帽舍不得摘,估计也不敢摘下来。“怕露出秃光蛋来”一一我们背后没少笑话他。其次,他长得不讨喜也就罢了,还挺能装,装成个大干部的派头,天天绷个脸,喜欢开会,讲大道理,讲理论,还讲不出个所以然来。第三,喜欢训人,借训人耍威风,摆架子。他没训过我,却训过另几个人,另几个有点恨他,另几个的心里话,就你还训俺们,你也配!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他很少下地干活。瞧瞧人家冯场长,老人家那么一把子年纪了,不管干什么活,都是身先士卒,从不含糊。再看这王书记,也不知他天天都忙些啥,下地干活,难得见到他。 我们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我们这些人。我们(主要是那几个被他训过的)有意无意地搞过恶作剧捉弄他,让他也吃了苦头。 那年的中秋刚过,上面通知说,有两个逃犯逃到了林场这一带,要求场里夜间设伏,争取逮住那两个逃犯。 我们理所当然的都是基干民兵,执行这样任务是带枪的,虽然两人一支枪,也还是很令人兴奋的。 终于轮到我们这一组值更了。那天夜里,本来应是5个人,带队的是贫下中农,4个是知青,其中有俩是“另几个”之中的。巧的是那位贫下中农突然病了,临时找人代班又找不到,只好让我们四个带2支枪,一人一件军大衣,上山了。 山上有一条小道,是通行山前山后的必经之路。我们的任务就是守住这条小路,不让可疑之人通过。不过,说实话,说那两个逃犯会跑到这儿来了,我们心里都不相信,逃这儿不是被逮着就是被饿死,傻呀?但这个话,谁都不敢说,这可是书记亲自抓的。 这且不管他,咱服从命令听指挥,来值这个更就是。可长夜漫漫,白天干了一天活了,累,睏得不行。咋整?也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将蔓延在尺把宽小路两边的草系起来,隔一两步就系一个,黑灯瞎火的,逃犯真来了,肯定会被绊倒,摔个嘴啃泥。咱们放心睡咱们的,他一摔倒,动静小不了,咱爬起来,轻轻松松就摁住了他。大家嘴上应着,说是好办法,确实是好办法。心里都在乐,哪来的逃犯?逃犯来不了,书记肯定会来! 行文至此,我应该写道:果然,后半夜,书记来了,连续摔了两个大马趴,被我们按在地上…起来后,他还不得不表扬我们警惕性高责任心强法子好…… 实际情况是,我睡着了,裹着军大衣睡得老香了,什么也没听到,更没看到。被他们叫醒时,见到了已经升起来的太阳。 不过,下山时,听他们断断续续地聊天,好像真的发生了上面行文中的事…… 3、会计 场里只有一个会计,姓甚名谁,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依稀记得好像姓甘。我尚清楚地记得,他个子挺高,不胖,长白脸,头发很黑很硬,眉毛很黑很浓,眼晴有些凹陷,不大,很锐利。他是一个瘸子,尽管他瘸得并不是很厉害。 我们知青刚进场时,就有人悄悄地告诉我们说,会计这个人的生活作风不好,乱搞男女关系。 闻听此言,我们一致认定,他的腿肯定是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被人打断的。于是,我们很鄙视他,也很疏远他。 一直等到过了很长时间,我们才知道,他的腿是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国鬼子打伤的。受伤后,他被美军俘虏了。在战俘营,呆了很长时间。直到双方交换战俘,他才得以回到家乡。 在战场上,在弹尽粮绝的时刻,他也想过要“杀身成仁”。可他办不到啊!一次,他喝多了酒,很伤心很无奈地对我们说,美国鬼子个子高,胳膊长,力气大。你和他拼刺刀,他根本不跟你拼什么刺刀。他只要抓住了你的枪管,就势一带,就能紧紧地抱住了你,你丝毫动弹不得,手动不了,你的脚也沾不着地,你想拉手榴弹的弦与他们同归于尽,根本办不到,想死你都死不了。 回到家乡的他,不仅不能享受英雄的荣誉和待遇,没有工作,没有应有的补助;反而因为被俘这件事,成了他终身无法洗去的耻辱和无法摆脱的麻烦;与他十分相爱的姑娘也因此而远嫁新疆。没有一个好女人喜欢他,更没有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他。 后来,他和一个寡妇“好”了。这也就是他生活作风不好的由来。 他是个文化人,曾经有过一个预测,对我说过。他说,在这拨知青中,你(指我)和涛会有一番作为。 现在看来,他的预言对了一半,涛那一半是对的,我这一半叫他失望了。(待续) 最忆是巢州扫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iangfencaoa.com/lfcpzff/10691.html
- 上一篇文章: 走进深山,探寻ldquo仙草rdq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